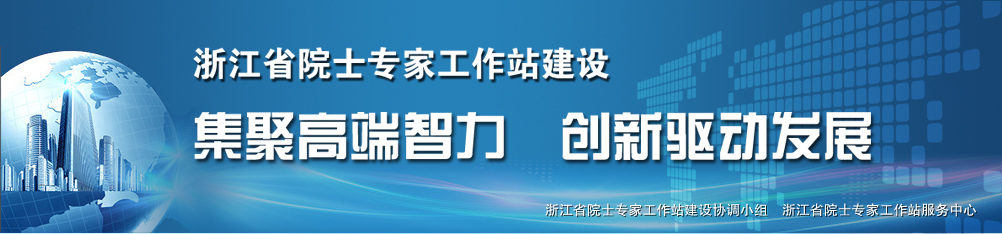“科学+”特别节目:科学思辩---安乐死能否合法化
来源:科学+项目组 发布时间:2013-11-07
生老病死,是每一个人都会亲身经历的事,当一个人得了绝症,虽生犹死,他是否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?6月8日晚,“科学+”特别活动,来自浙江工业大学和浙江理工大学的两支辩论队,围绕 “安乐死能否合法化”这一命题展开唇枪舌战。赛后,来自医学、伦理、法律三个领域的专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各个层面的剖析。

唇枪舌战:安乐死,善莫大焉?
安乐死源于希腊文,意思是"幸福"的死亡,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病危状态下,因不堪忍受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,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,经医生认可,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。
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。安乐而死,善莫大焉。”作为正方的浙江理工大学辩论队,以简短的开场白,阐述了己方“安乐死应该合法化”的观点。他们认为,安乐死能帮助人摆脱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,是对于生命的尊重,对人权的肯定,合法化有其合理性,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,安乐死立法的条件不断完善,安乐死的合法化必是大势所趋。反方浙江工业大学辩论队的同学则认为,生命的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,而安乐死的执行本身就是由被执行之外的意识主体所操纵,带来的不可控性和风险会很大。生命可贵,即使遭受痛苦仍坚持活着,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。辩论共分双方立论、双方互相提问、双方四辩总结陈词三个阶段,双方辩论队员各持己见,旁征博引、唇枪舌战,一时难分高下。队员反应之快,辩论之激烈,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。
激烈的辩论赛后,三位来自医学、伦理、法律三个领域的专家,分别从他们专业的角度,对安乐死这一现象进行了各自层面的剖析。
医学现状:临终关怀逐步被社会公众接受
来自浙二医院的张茂博士介绍,全球每天至少有500万癌症患者在遭受着疼痛折磨,其中50%为中至重度疼痛,30%为难以忍受的疼痛。
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,病人的心跳、呼吸等生命体征都可通过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,但若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,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最终都会发展为心脏死亡。因此,与心脏死亡相比,脑死亡显得更为科学,脑死亡标准出台的意义在于:可挽救更多的生命,使医疗资源分配更合理,满足器官移植的需要,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。
安乐死在国外较为普遍,指如果病人在意识清醒时做出“在心脏停止时不救治的决定”,那么在医生就会尊重他的意愿。近年,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在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内,减轻症状的医疗护理—临终关怀逐步被社会公众接受。
张茂博士还介绍,虽然安乐死在国内并未合法化,但一些医院,根据病人家属与本人意愿,并签字确认之后,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病人实施谨慎的“限制性医护措施”:即仍然对患者进行积极的化疗、手术甚至住进重症监护病房,但当心跳停止时不进行胸外按压和呼吸治疗。
伦理困境:安乐死面临着理性和情感的冲突
安乐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,而是一个复杂的、困难的、前沿性的伦理学问题,安乐死挑战中国传统道德。“中西方在价值观上有很大的区别,东方普遍认为集体大于个人;西方的价值观里,个人往往被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。这就解释了,安乐死在西方更容易被接受的原因。”来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郭俊伟博士介绍说,荷兰是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西方国家。而在亚洲,日本是唯一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。
郭博士抛出了一系列问题:“我们提到临终的尊严,到底活着是不是身为人最大的价值?活着,究竟是说你的精神活着,还是你的肉体活着?在当下,也许多数人是两者并存的。但当有些人,可能精神和肉体只有一种存活的时候,他有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是否要继续活着?”的确,安乐死问题面临着理性和情感的冲突,陷入了伦理的困境。
法学观点:安乐死的立法非常慎重
“安乐死的合法性争议,核心问题就是:公民是否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。”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李华副教授,从法律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。
她认为,从立法上要确立安乐死是否要合法,最大的担心就是安乐死被滥用。因为安乐死一旦成了法律,确实会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规则来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情况。荷兰七千多例实施安乐死的事例中,有41%是家属提出申请的,当中出现了很多人,为了躲避安乐死逃到国外去的情况。老人们甚至开始不信任医生,甚至不信任家人。
“澳大利亚在1996年的北部议会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,但在实施了八个月以后就被废除掉了。”李华副教授说,全球真正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非常少,她认为,对安乐死的立法要非常慎重的。
李教授还介绍,我们国家目前的立法是不支持安乐死的。但大部分安乐死的案件,被告都被处以缓刑,表明了国家在对这类行为的处罚上的轻刑化的立场。
的确,安乐死是一个复杂且具争议的话题,在医学、社会、法律上都存在难题。
本次“科学+”特别节目,引入了科学思辨这一形式,辩论赛和专家理论剖析有机结合,比一般的辩论赛更具理论深度,又比传统的专家报告会生动活泼,不失为一种科普活动的有益尝试。